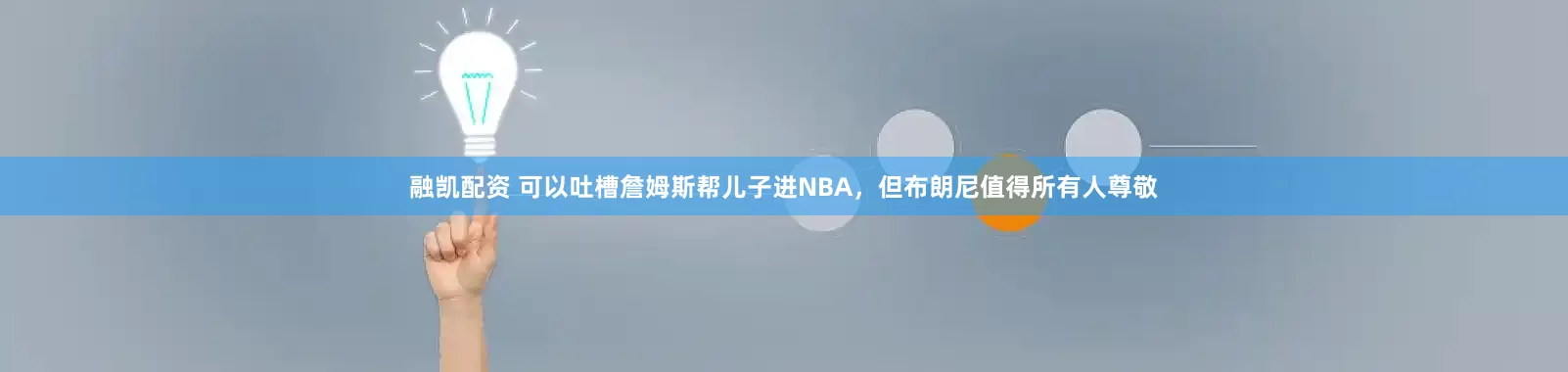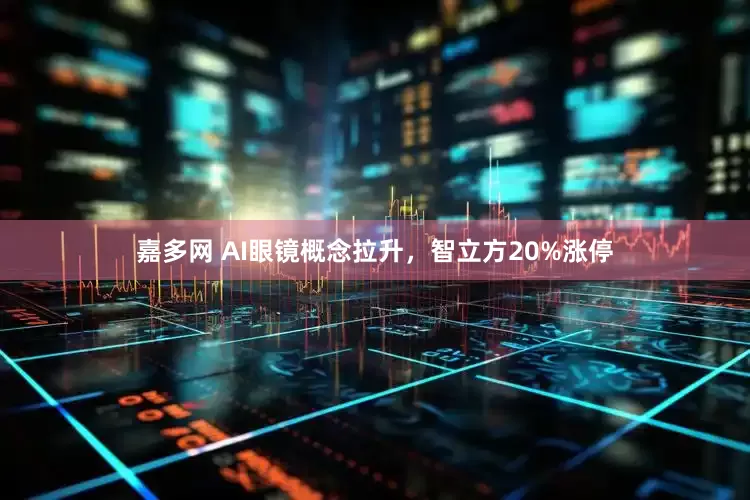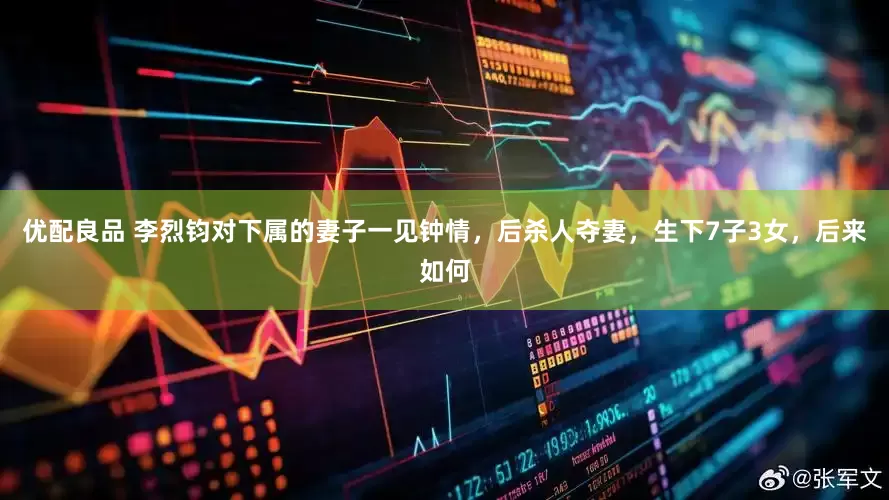
“1934年冬夜,这碗桂花酒你到底喝不喝?”客厅里,孙道仁盯着对面的李烈钧,语气像在开玩笑,却又暗藏火药味。此时两人距离第一次并肩作战已过去二十多年优配良品,杯中酒却一点也不温暖——因为桌面下压着一封写给蒋介石的密信,内容直指一桩旧案:副官龚永被诛,以及那位早已改口唤李省长为“先生”的女子。

时间往前推十三年。1921年初夏,江西都督府里办公厅刚装上电灯,李烈钧正埋头批示。不远处的龚永拿出一张新婚合影,得意洋洋:“世琦才学不输男子,你看。”灯光打在相片上,女子一袭洋装,眉眼灵动。那一秒,李烈钧的目光停顿,比电灯泡还明亮。之后的事,像被拉开的闸门,洪水再也关不住。
不得不说,李烈钧当时的权势在江西省内几乎没人敢碰。外人对他印象是“爽朗、讲义气”,可爽朗背后常藏锋利。龚永办事勤勉,却有显摆的毛病,三天两头在人前举着妻子照片夸口。兄弟情因一句句炫耀变了味,嫉妒在李心里发酵,比正在整修的都督府墙角的石灰还要灼人。

1922年春优配良品,北洋系暗潮汹涌,各方都在找筹码。李烈钧手握机密,自创一套局:让龚永单人携带文件奔赴福州。表面是“立功机会”,暗里却早已写信给水陆都督孙道仁,指称龚永暗投袁世凯残部。军令如山,当夜龚永登岸即被羁押,三日后枪决。执行前他只说一句:“我若真叛国,何必独来?”枪声隔着闽江传出老远,却没惊动江西的夜。
李烈钧收到回电,假意痛哭,随即大张旗鼓派人吊唁,又三次登门抚恤遗孀华世琦。那时她不过二十岁,守寡的日子像漫长雨季。李烈钧一步步化身“长兄”,送米送药,为其兄长谋得税务所差事,还允诺支付全部学费给华家的两个侄儿。情感就在恩义包装里发芽,1930年两人正式成婚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李家本有正室,可他依然给华世琦建洋房、配小汽车,几乎所有公开场合都挽她的手臂出现。旁人背后议论“侧室当家”,却没人敢当面多话。七子三女先后降生,李烈钧给孩子起名都带一个“世”字,仿佛要把对龚永妻子的偏执彻底写进家谱。
真相终究有浮出水面的一天。1933年秋,孙道仁与旧识在南京聚餐,几杯黄酒下肚,突然拍桌怒骂:“李某何止能打仗,更能害命。”话出口才发现席间有人记着速写。流言以惊人的速度传回重庆、上海,乃至广州码头。李烈钧选择沉默优配良品,他清楚,政坛上最锋利的不是刀,是时间,一阵风就能把新闻吹散。
华世琦得到风声时正在上海法租界给长子买西装。她回到旅馆,关门坐了一夜,天亮仍旧照常梳头、出门。她没提离婚,更没自尽,只对闺蜜说过一句:“我已无退路。”与龚永的婚礼她记不清细节,对李烈钧却有十年相守和十个孩子,这种重量足以改变选择。

抗战爆发后,李烈钧把五个儿子送上前线。一纸保送令,他亲笔签名,末尾加注“生死以国事为重”。前线传来阵亡名单,他也只是皱眉数秒,没有掉泪。有人揣测这是他在赎罪,也有人说这正是军人本色。哪种解释更接近真相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1946年2月的重庆寒潮让他的旧伤彻底爆发,最终病逝在嘉陵江畔的官邸。
治丧那天,下着小雨,灵柩前站着华世琦和存世的两个儿子、三位女儿。她神情恍惚,却没失态,只轻声吩咐:“别让客人淋湿。”有人暗暗佩服,这女人心性之稳,比不少沙场老兵还强。

至于那桩“杀人夺妻”的旧案,国民政府既未追查,也未公开澄清。资料里只留下两份彼此矛盾的供述——一是李烈钧给孙道仁的密信,二是龚永临刑前的口供,两者中间隔着一条再也填不平的沟。民国史料多如烟尘,这页纸却显得格外模糊。
后来如何?华世琦带着三个孩子去了香港,办了小型外贸公司。1958年,她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:“往昔事不再提,读书育子才是真。”十年后病逝,墓碑刻的是“华贤淑女士”,未标注任何夫姓。

史家评论李烈钧,离不开讨袁、护法、抗战,也绕不开这一段私德阴影。功与过像硬币两面,一面闪亮,一面锈迹。究竟哪面更重?或许只有历史自己说得清。
配先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